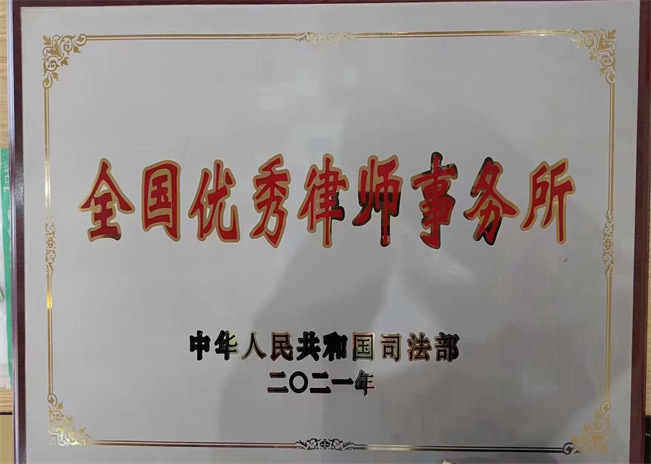通过以上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晰的看出,由于刘某不是卖淫场所的组织者、所从事的行为不是组织者的行为、不能行使组织者的决定权、没有获得与组织者身份对待的利益,因而刘某根本不是卖淫团伙的组织者。而且,在卖淫小姐与卖淫团伙中,也没有人把他看成组织者,刘某自身无论是从主观还是客观上也“组织者”,因而,以“组织卖淫罪”对刘某进行指控明显是不合适的。
(二)刘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所谓的“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予以帮助的行为,本罪客体与组织卖淫罪相同,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人卖淫的行为。“协助组织卖淫”,是指卖淫活动组织者以外的人,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所谓“其他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充当保镖、皮条客、管账人以及为他人组织卖淫看门望风、提供场所、指示目标、排除障碍等。关于上述内容,是所有刑法教科书在解释“协助组织卖淫罪”时的共同认识,我们在司法适用时也惯常性都是据此认定的。
而且,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第四条 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从中不难看出,只要行为人不是卖淫团伙中的组织者,并且为该卖淫团伙提供了帮助的非组织行为,则应被界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刑法原理和刑事立法上属于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但刑法已将该帮助性质的行为剥离出来,赋予新的罪名。因此,对协助他人组织卖淫的和直接帮助他人卖淫的,不能再以同一罪名的共同犯罪论处,而应该分别定罪和量刑,即对组织者定组织卖淫罪,对其他协助人员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通过上述多个层面的分析,辩护人认为,刘某根本不是该卖淫团伙的组织者,因而理当不能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但是,刘某在该卖淫团伙中行使了一定事务性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力,为该犯罪组织的延续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二、刘某的行为更不属于协助组织卖淫罪中的“情节严重”情形,对刘某应当在基本法定刑的幅度范围内适用刑罚。
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
第五条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协助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招募、运送或者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就本案涉及的情形来看,刘某并不具有上述的任何情形之一,因而在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情形不具备的情形下,我们只能认为刘某的协助卖淫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而只属于358条第4款的基本法定刑,即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档次内适用刑罚。
(二)刘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刑法第358条第3款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所谓的“协助组织卖淫罪”,是指明知他人组织卖淫而予以帮助的行为,本罪客体与组织卖淫罪相同,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各种方式帮助他人卖淫的行为。“协助组织卖淫”,是指卖淫活动组织者以外的人,为组织卖淫的人招募、运送人员或者有其他协助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所谓“其他协助组织卖淫的行为”,实践中通常表现为充当保镖、皮条客、管账人以及为他人组织卖淫看门望风、提供场所、指示目标、排除障碍等。关于上述内容,是所有刑法教科书在解释“协助组织卖淫罪”时的共同认识,我们在司法适用时也惯常性都是据此认定的。
而且,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第四条 明知他人实施组织卖淫犯罪活动而为其招募、运送人员或者充当保镖、打手、管账人等的,依照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的规定,以协助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不以组织卖淫罪的从犯论处。”
从中不难看出,只要行为人不是卖淫团伙中的组织者,并且为该卖淫团伙提供了帮助的非组织行为,则应被界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在刑法原理和刑事立法上属于组织卖淫罪的共犯,但刑法已将该帮助性质的行为剥离出来,赋予新的罪名。因此,对协助他人组织卖淫的和直接帮助他人卖淫的,不能再以同一罪名的共同犯罪论处,而应该分别定罪和量刑,即对组织者定组织卖淫罪,对其他协助人员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通过上述多个层面的分析,辩护人认为,刘某根本不是该卖淫团伙的组织者,因而理当不能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但是,刘某在该卖淫团伙中行使了一定事务性工作,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力,为该犯罪组织的延续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应当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二、刘某的行为更不属于协助组织卖淫罪中的“情节严重”情形,对刘某应当在基本法定刑的幅度范围内适用刑罚。
根据2017年7月25日起施行的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3号)
第五条 协助组织他人卖淫,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五十八条第四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一)招募、运送卖淫人员累计达十人以上的;
(二)招募、运送的卖淫人员中未成年人、孕妇、智障人员、患有严重性病的人累计达五人以上的;
(三)协助组织境外人员在境内卖淫或者协助组织境内人员出境卖淫的;
(四)非法获利人民币五十万元以上的;
(五)造成被招募、运送或者被组织卖淫的人自残、自杀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
就本案涉及的情形来看,刘某并不具有上述的任何情形之一,因而在司法解释明确列举的情形不具备的情形下,我们只能认为刘某的协助卖淫不属于“情节严重”的情形,而只属于358条第4款的基本法定刑,即在“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的法定刑档次内适用刑罚。

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是西南地区首家刑案专业化律师事务所,团队旗下汇聚了一大批知名刑事律师、法学专家、博士等人才为确保办案质量,智豪律师作为首家向社会公开承诺所承接刑事案件均由律师专业团队集体讨论,共同制定团队辩护代理方案——“集体智慧、团队资源”,结合刑事领域积累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关系资源及刑事辩护的实战经验,“为生命辩护、为自由呐喊”。
免责声明
本网未注明“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的文/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出于传递更多信息之目的,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下载使用,必须保留本网注明的“稿件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如擅自篡改为“稿件来源:重庆智豪律师事务所”,本网将依法追究责任。如对稿件内容有疑议,请及时与我们联系。 如本网转载稿涉及版权等权利问题,请相关权利人根据网站上的联系方式在两周内速来电、来函与智豪团队联系,本网承诺会及时处理。